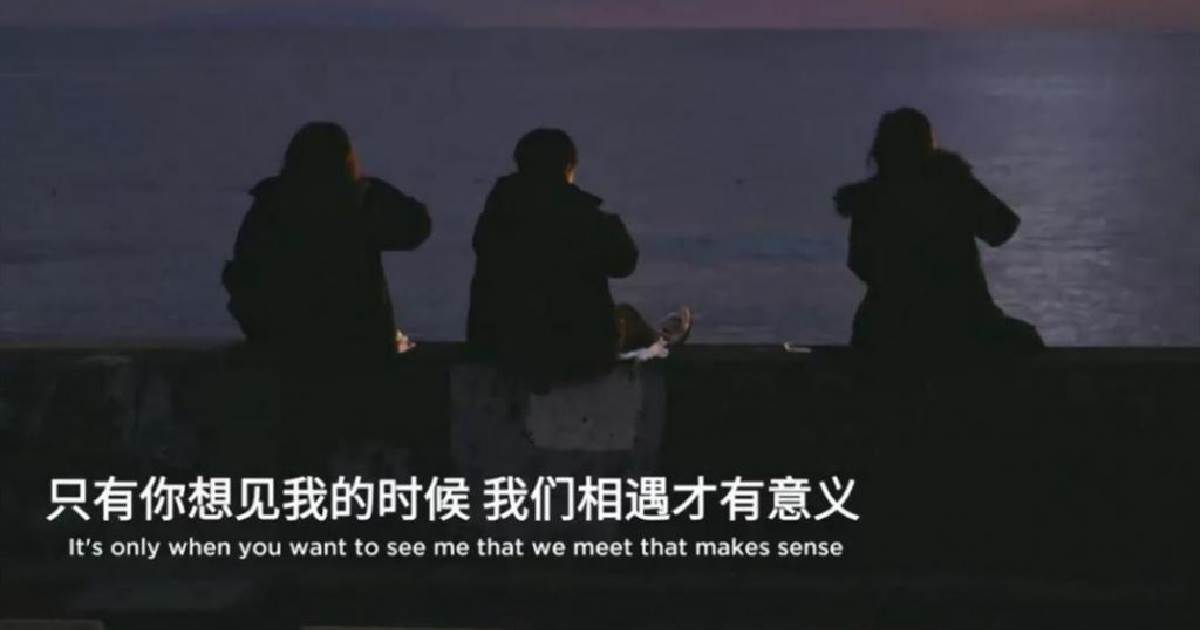付:15.00$/季,50.00$/年開通VIP會員
享:全站無廣告,送合作漫畫、短劇、福利文、VIP會員
點擊開通VIP,瞭解詳情>>
《高端狩獵局》第6章
還與他在無人的教學樓里私會。
將他推在座椅上。
拽著他的衣襟,讓他被迫揚起高傲的脖頸與我親吻。
池燼那邊,雖然不滿我與江聿風與時逾走得「太近」。
但只要我一雙眼幽幽地看著他,吸著鼻子就要吊嗓子的時候,他就頭痛地舉手投降,表示只要我不哭,一切都好說。
在昏暗的電影院里,我笑瞇瞇地挽著他的胳膊,裝作不經意地在他耳邊說話。
就連出了電影院,他那一向猖狂至極的臉,依舊紅到了耳根。
誰能想到換女友如衣服一樣勤的校霸,竟然如此純情。
而時逾的英語教學到期后,又給我續了好久。
在教他特殊語法句子時,轉過頭便對上了少年迎上來的唇。
我象征性地掙扎了幾下,又無力地垂下了軟綿的手。
就這樣來來往往。
江聿風帶我去公證處想要過戶給我一套房子,問我畢業后要不要搬出去和他一起住。
池燼交給我他的銀行卡,別捏地說這樣我就能拿捏他,將他管住。
時逾偷偷地給我打了好幾倍的家教費,讓我能不能多陪陪他,每天不要走那麼早。
直到三個月的最后一周。
嬉笑吵鬧的學校里。
我被人掛在了表白墻上。
但上面的文字并不是對我表達愛意。
而是——
「金融系大三的林棠,你別得意了,江聿風、池燼、時逾他們三個追你就是一場賭局,你有什麼好裝清高的?不過也是他們三個的玩物和舔狗,真是賤得可以!」
一句話,不僅讓這場游戲的賭約正式地浮出水面。
也讓他們三個想要努力隱瞞的秘密呈現在我面前。
更是讓他們三個不約而同地。
——急了。
15
我的手機被消息和未接來電裝滿。
江聿風:「棠棠,你在哪兒?我們談談!」
猜你喜歡
溫馨提示
加入尊享VIP小説,享受全站無廣告閲讀,海量獨家小説免費看
進入VIP站點

 上一章
上一章
 下一章
下一章
 目录
目录
 分享
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