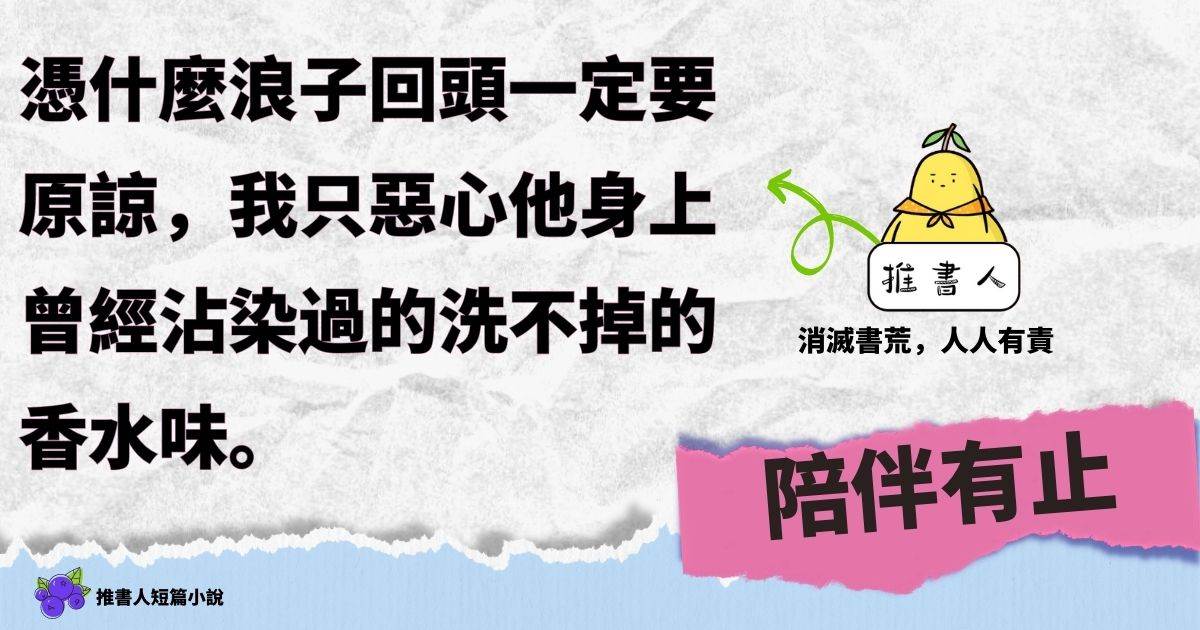付:15.00$/季,50.00$/年開通VIP會員
享:全站無廣告,送合作漫畫、短劇、福利文、VIP會員
點擊開通VIP,瞭解詳情>>
《陪伴有止》第1章
當我從酒吧中找到喝得爛醉的晏殊玉時,他正閉著眼玩笑般地將唇印在身旁打扮火辣的女生臉上。
我當時攥著他的領子問他為什麼變成了這樣,我質問他蘇瑾有什麼好的。
他怔了怔,忽而開始流淚,他告訴我:
「因為她是蘇瑾啊……」
后來他又成了年少有為的晏總,只是自那以后的桃色新聞成了他的增色。他隨機找到一個合眼緣的人,隨機開展一段速食的激情。
最后再讓我送去名貴的分手禮物。
他跟我說:「槿槿,你看,我仍舊過得很好。
可他不知道他當時的神情,落寞得像是個被拋棄的小孩。
我曾經因此而憤怒、嫉妒、痛苦,又可悲地從「他不會愛上除蘇瑾以外的任何人」的事實中得到一絲竊喜。
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,我竟然感到了麻木。
他的通話仍然沒有中斷。
我聽見他憤怒地讓電話那端的女人離開,又可憐巴巴地握著聽筒:「我想回家,槿槿。」
「你來接我回家好不好?」
不知是習慣還是其他原因,我總是無法拒絕他。
可我其實有點想笑,你的家又不在我這里。
打給我干什麼呢,晏殊玉?
2
我果然在酒店里找到了喝得爛醉的晏殊玉,那個電話里女聲的主人不知道去哪里了。
只剩下晏殊玉,他的衣領上還沾著半成型的口紅印,乖乖坐在沙發上等著我接他回家。
許久之前,我總是在酒店門前接到一身清爽頭發還沾著濕氣的晏殊玉。
那時候我每每看見,心總像破了個洞,呼呼地灌進冷風,讓我四肢發冷。
我總是站在他身后,等著他時不時到來的激情,然后為那些和他相擁入眠的女人挑選精美的各種禮物。
現在我的隨叫隨到倒更像是一種習慣了,陪伴他十一年所養成的習慣。
猜你喜歡
溫馨提示
加入尊享VIP小説,享受全站無廣告閲讀,海量獨家小説免費看
進入VIP站點

 上一章
上一章
 下一章
下一章
 目录
目录
 分享
分享